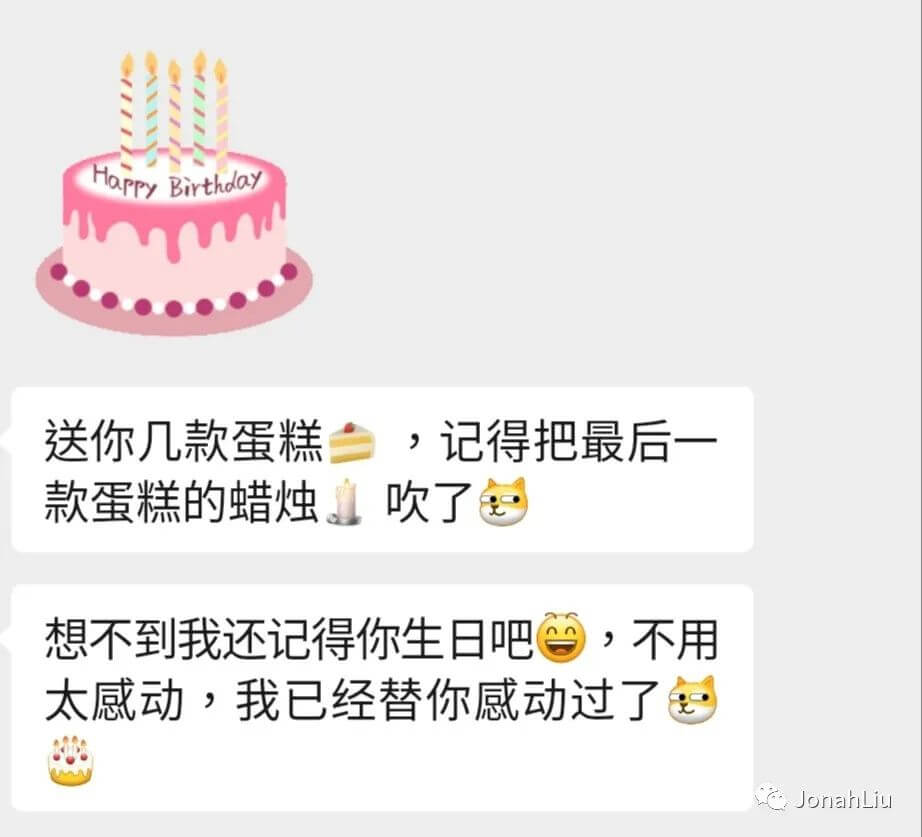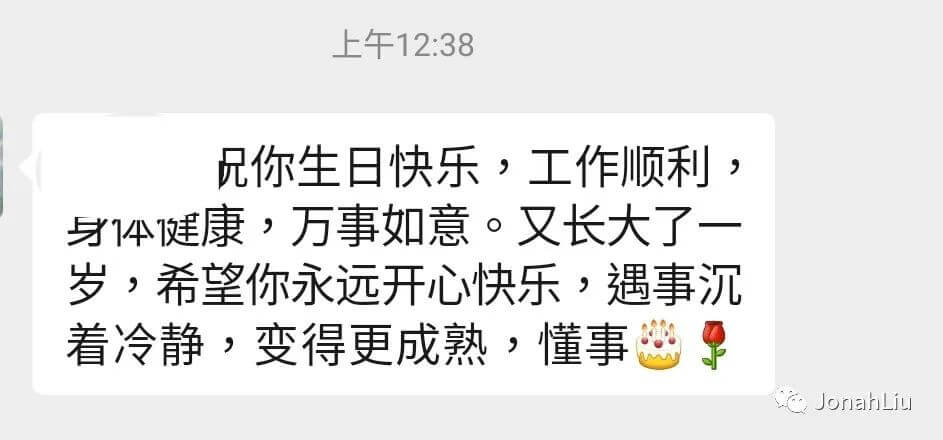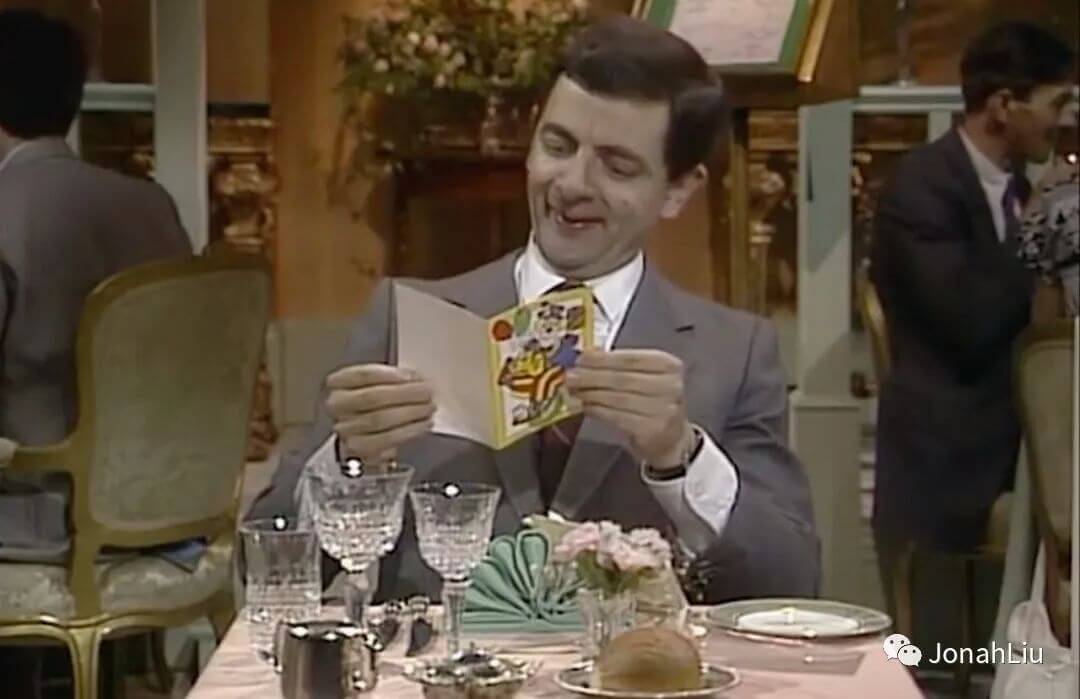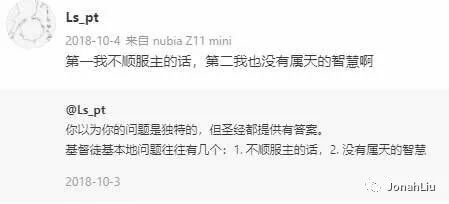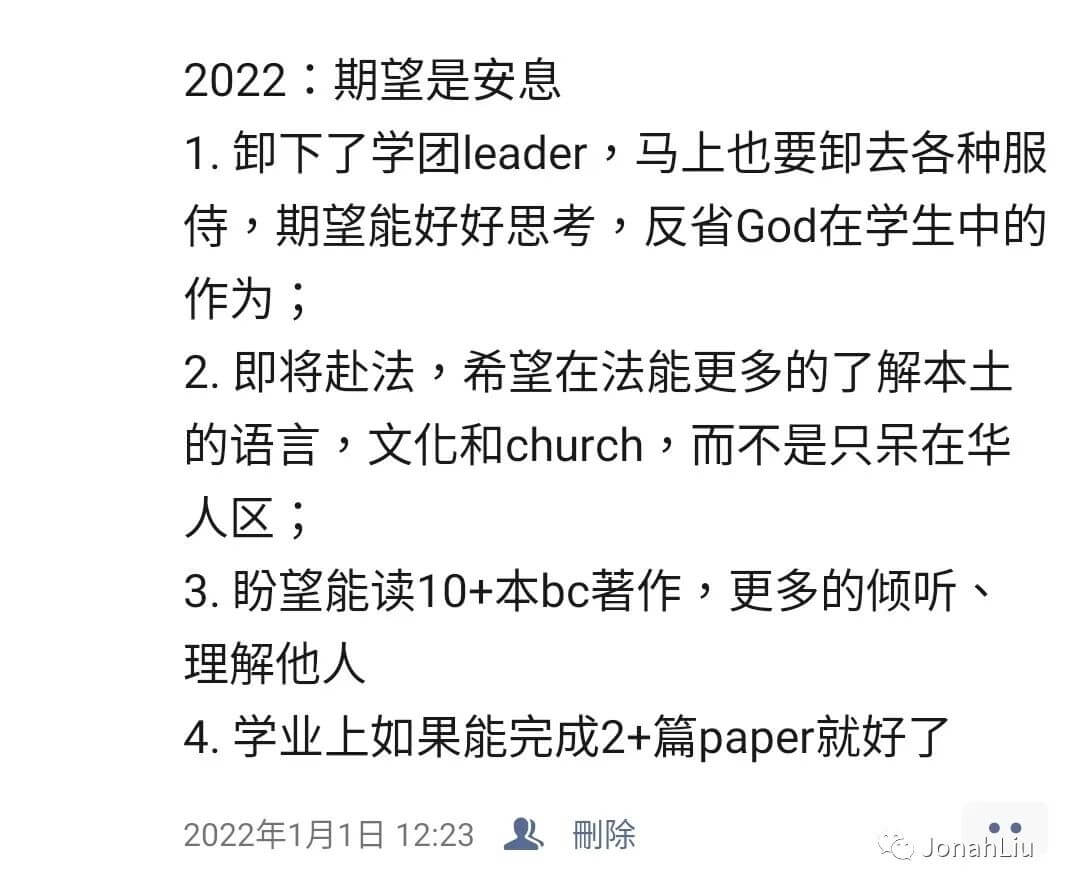本篇关于喜新厌旧。
私酷鬼写到:
你那病人朝夕相处的那伙人的真正麻烦之处在于,他们纯粹是个基督教团伙。他们当然都有个人利益,但彼此间仍旧单纯以基督教信仰为纽带。
按我活在地上不多年日里对友谊的理解,大概有三种原因会让两个人成为朋友:有共同的利益、有共同的兴趣、或是有着共同的信仰。第一种朋友会随着年龄的成长、社会阅历的积累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,点头之交笑面藏刀;有着共同兴趣的朋友关系最浅,但也最为长久,可以因某个活动招之即来,但活动过去往往也很少再联系;共同信仰的朋友最难描述,可以是生死之交,也可以淡如水,但久别重逢之时常常不觉别离了许久。
信仰是一个跨越时空的纽带,因着一主、一信、一洗、一神,让各族、各方、各民彼此连接,无论是过去的、现在的、还是将来的。
宗教改革最根本的诉求就是:让基督教回到使徒和教父时代那样纯粹的基督信仰。唯独圣经、唯独基督、唯独信心、唯独恩典、唯独神的荣耀,这是最初使徒和教父们所传承下来的信仰。而人心总是不满足,想要在这些东西上添一些什么:比如,信心和律法——尽管保罗从很早就开始驳斥这些;比如,圣经和风俗;比如:
基督教和危机、基督教和新心理学、基督教和新秩序、基督教和信仰疗法、基督教和灵媒研究、基督教和素食主义、基督教和简化英语拼写运动等等。
魔鬼写道:
如果他们非要做基督徒不可,那至少让他们做有特色的基督徒。
推崇原教旨主义者的笔者,始终认为偏离了原始定义——比如冠之以“特色”——本质上是另一个东西了。比如,法式中餐不是中餐;中式西餐也不是西餐……
当然魔鬼是洞察人心的,私酷鬼继续写到:
喜新厌旧是我们在人类心灵里制造出来最有价值的情绪之一——它可以引发宗教异端、政见短视、夫妻不贞、朋友失信,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。……人类生活在时间里,而且要按照一定的先后次序来体验真实。因此,为了进一步体验真实,他们就必须经历很多不同的事情,换句话说,他们必须经历变化。……祂挖空心思地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把变化和永恒结合起来,造出一种我们称之为节律的东西,以此来满足这两种喜好。
三个月之后再次捡起这篇草稿时,对“喜新厌旧”这个主题有了异样的理解。
我完全认可人类心灵里对变化的渴望:当每日的生活变得单调与重复之时,就渐渐变得乏味;曾经美好的风景开始流于平常,曾经对工作的兴趣与渴望开始被日复一日的劳作磨平,不断重复的每日生活也渐渐的失去光彩。
平凡并不足为惧,日复一日的重复才最可怕。当一切都开始一成不变之时,就开始渴求一些变化,一些称之为“新鲜感”的东西。这种情绪被魔鬼挑逗夸大,就会在心中渐渐滋生出对“永无止尽、毫无规律变化地”欲望。这是堕落的起头。
如果我们(魔鬼)玩忽职守,人们不仅会在今年一月份的雪花,今天早晨的日出,今年圣诞节的李子布丁里体会到新鲜和熟悉相互交织带来的满足感,而且会陶醉其中。
魔鬼的头脑比我们更加懂得这其中的奥秘:
首先,它在削减快乐的同时助长了欲望。新鲜感所带来的快乐从本质上说,比其他任何事物更易受到收益递减率的支配。……其次,越是对新奇贪得无厌,就会越快的耗尽所有纯真快乐的资源,然后就会转而渴望那些受到仇敌禁止的快乐上去。
私酷鬼诚然是对的。新鲜感所带来的快乐比其他任何事物都容易失去。当不断寻找新鲜感之后,人终会变得乏味,开始无法忍受现状——直到,想要推翻维持现状的所有。
前几个月中,生活的乐趣被每天不断尝试的新的饭菜所承包。但这种乐趣在两个月后“智力枯竭”的焦虑所笼罩;而后,新鲜感被工作make progress所代替,可当工作遇到瓶颈,那种挫败感所带来的难过也是成倍的……
人总是不容易被长久的满足。欲望(哪怕是正常的欲望)就像一个无底的黑洞,你永远也无法填满,当你望向它时,只觉得深不见底的恐惧。
谁能满足这无尽的欲望呢?谁能填满这黑洞呢?
很遗憾,路易斯并未直接给出答案,也为给出面对这种“不满足感”的解药。他只是写到:
据我所知,祂希望人们在考虑哪些被提到做面上的行动方案之时,先去问一件非常简单的问题:这是否符合公义?这是否审慎有智慧?这样可行吗?而我们若能让人不断的问“这是否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潮流?这是进步还是倒退?这是历史前进的方向吗?”,人们就会忽略那些有价值的问题。
前一段上课时,发现圣经给许许多多“情绪和欲望问题”了一个相似的解药(当然细节上有所不同以及这不是唯一一剂解药):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尽上帝要求人所当尽的本分。乍看圣经似乎答非所问,但千百年来的实践以及圣徒的传承向我确证,圣经中远超人的智慧。也正如路易斯所写,首先要考虑的并非是这个变化的时代,而是那个不变的永恒。
但谁知道呢?或许在不断地经历与信仰实践之中才会愈发的确信。May God help us。